西王母形象谱系与文化的多维阐释--西王母及其文化内涵特质
西王母作为上古神话传说时代生活在我国西部的一位人文始祖,在与中原文明不断碰撞交融中,其形象经历了从半人半兽的部落首领、化育万物的创世女神、高居显位的女仙之首,再到民间慈母的多次转变,衍生出的“母爱众生、和平交融、富贵长寿、团圆亲善”等文化内涵特质,历经千年积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历史内涵与民族情感,在海峡两岸人民的文化传承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符号与精神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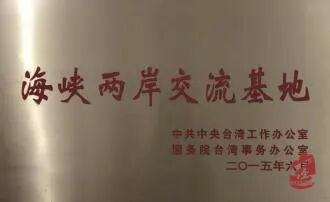
西王母,又称“瑶池金母”“王母”“金母”,或“王母娘娘”。从中华文明多元交融的文化体系来看,不同历史阶段的西王母也被赋予了不同角色,不仅是远古时期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与部族首领,也是上古神话体系中一位兼具多重神格的女神,同时也是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女仙之首,是历史人物神话化、宗教化和民俗化的典型。其形象演化与历史、文化、政治、思想息息相关,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和社会需求。

一、千面女神:西王母形象的历史嬗变
在我国历史上,西王母形象演变贯穿中华文明进程,上古时期作为虎齿豹尾的氏族首领、图腾神祇;先秦时期《山海经》中演化为执掌灾厉五刑的昆仑女神;汉代将其升华为创世母神与长生象征;道教兴起后尊为统领女仙的至尊神“金母元君”;明清以降民间信仰中则化身为慈爱温厚的“人间母娘”,融入庙会、祭祀等民俗活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的不同形象使西王母在神话、历史与文化的交织中具有多重概念。
(一)西王母是部族首领与西方古国的双重指称,体现了民族和睦共处的价值观。殷墟甲骨文中出现的“西母”一词,被认为是西王母的早期称谓。《山海经》中描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可见先秦时西王母形象基本上是人的形状,同时带有兽形的外部特征。而在上古时期,部族首领同时也兼具“大祭司”的职能,“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上古时期西王母部族与天地沟通的图腾角色扮演。近代以来,吴晗等学者考证,西王母实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活跃于陕甘高原一带戎或西戎的别称”(有学者认为以泾川为中心)。至汉晋时,“西王母国”作为政治实体首见于辞书之祖《尔雅·释地》,则有“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的记载。可知这里的“西王母”是作为地名出现的,指的是西方古国或部族首领的称号,而非单一人物。这也就解释了其为何能跨越从上古时代延续至周穆王时期的漫长历史维度。从《竹书纪年》《大戴礼记》《尚书大传》等书的记载可见,西王母演化成了一个人间帝王的形象,作为国王的她及她的“国家”,和周边“国家”往来极其频繁。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在泾川“瑶池对歌”的记载(见于《穆天子传》),更被视作早期部族外交的史实投影。
(二)西王母是创世女神和昆仑秩序的缔造者,折射出华夏文明早期的宇宙观。《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在这里,西王母成了昆仑之丘的神人。昆仑在神话中被视为“天地之纽”,既是宇宙的轴心,也是万物生发的源头,昆仑之丘“万物尽有”,为西王母后来成为创世女神和昆仑山的主人打下了基础。到了《穆天子传》中,周穆王征伐西戎部落,并且在昆仑山拜访了西王母,此时西王母已经具有了更浓厚明确的华夏西部人文始祖和昆仑女神的意味。甘肃泾川流传的创世传说中,西王母以宝针划开混沌,释放日月之光,以羊角枝沾泥造人的故事,又暗合了“天地洞开”“土生万物”的原始信仰,其创世神格与夸父开天、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形成呼应。在殷商卜辞中“西母”与“东母”的对称祭祀,表明其已被纳入中原文化的早期宇宙观,象征着位于中原西方的神祇,折射出华夏先民对生命起源的想象和世界本质的深刻思考。
(三)西王母是道教体系中的女仙之首,体现着道教文化“阴阳平衡”的和谐理念。在道教诞生后,西王母作为除女娲外为数不多的上古女性神话人物,优先被道教接纳并做了适应性改造。西汉时期,其从“豹尾虎齿”的半人半兽形态重塑为“天姿掩霭,容颜绝世”的雍容女仙。南朝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将其列为第二阶“女真位”之首,唐代《墉城集仙录》称其为“女仙之宗”,统领墉城仙境。作为女仙领袖,其地位仅次于“三清”,统领三界十方所有得道女性,并负责监察众仙行为,扬善惩恶,并传授道经秘法。如《五岳真形图》等灵文由其授予汉武帝,彰显其传经布道之责。民间信仰中,她执掌不死药与蟠桃,赋予信众长寿、平安之愿,这一职能亦被道教吸纳。自汉代武帝时起,西王母被官方建祠供奉,唐代时起,西王母祭祀被纳入官方仪典,凸显其在上层社会的神圣性。在男权主导的传统社会中,西王母能够被作为女仙领袖,与东王公(玉皇大帝)并称,共同执掌阴阳二气,化育万物,被人们崇奉。不但具有突破性意义,而且融合了宇宙本源、道德教化与女性权威,既是人们尊崇自然规律的象征,也体现了道教“阴阳和合”的宇宙观。
(四)西王母是民俗文化中的人间慈母,形成了中华民族“母性崇拜”的活态样本。“王母”之名隐含着“始祖母”的原始意涵。明清两代,与西王母有关的神话、信仰等文化资源,被民间教派融汇于宗教宝卷之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西王母形象和信仰发生了较大的分化,西王母的神格和信仰在宗教宝卷中得到空前的提升,从而形成了有关西王母新的形象与信仰。在《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瑶池金母金丹忏》《王母消劫救世真经》等宝卷中,西王母仍旧有明显的道教神仙色彩,但是民间在把西王母这位千年来在民众信仰中举足轻重的神灵引入民间宗教中时,将西王母的形象进一步世俗化、人格化。明清小说开始对西王母加以“人间皇后”的想象,成为民间信仰中一位慈母般的女神,时时向人间流露出慈母一般的关怀,这是明清以来西王母形象的显明特征。从上文论述分析,不难得出,西王母的母性崇拜并非单一维度的“温柔慈爱”,而是母系社会与原始母神的遗存、道教中的母性神格建构、民间信仰中的母性关怀、文化符号中的母性隐喻、跨文化视角中的母神共性相互交织塑造的结果,同时也受到农耕经济、儒家伦理、宗教文化的影响,既是中华文明伦理观、审美观和信仰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华民族性格中的温情与韧性的有力印证,其对生命、包容与和谐的追求,已融入现代社会的精神构建。
二、美善集成:西王母文化的内涵特质

西王母文化是一种深植于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逐步形成了以“母爱、和平、长寿、团圆”为核心的美善文化,涵盖神话、宗教、民俗等多个方面,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对生命、自然、权力与伦理的哲学化表达,既是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见证,也承载着人类对超越性价值的永恒追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母爱众生——始终贯穿着对生命关怀与博爱精神的极致诠释。西王母作为中华文明中极具母性魅力的女神形象。在神话与信仰体系中,她以“众生之母”的神格展现着女性特有的慈柔与坚韧:其掌管的“蟠桃”象征对生命的永恒守护,赐药救羿、接纳七仙女等传说传递着母亲对子女的救赎之爱,而道教典籍中“母养群品”的职能更将母性升华为滋养万物的宇宙力量。这种母性特质不仅体现在神话叙事中,更深深融入民间信仰实践——我国台湾省信众称其为“母娘”并献寿桃祝祷,泾川民众则通过庙会求子求孙、祈求子嗣平安,称其为“娘娘”或“老儿家”(当地对长辈的尊称),皆折射出民众对母性庇护的精神依赖。在当代社会,西王母文化展现出独特时代价值,她作为上古女性领袖的象征,为现代性别平等提供“刚柔并济”的典范;其博大母爱精神更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基因,中国台湾省数千家宫庙持续来回山西王母祖庙朝圣,印证着母性文化超越地域的凝聚力。
(二)和平交融——始终维系着跨地域、跨民族交融的精神纽带。西王母在中华文明史上始终扮演着和平使者的角色。在上古时期,西王母曾助黄帝战蚩尤、向尧帝献白玉环及疆域图、授舜帝《白玉瑗书》助其治国、助大禹治水等等,至周穆王西巡泾水上游与西王母“瑶池对歌”始,中原王朝便通过祭祀、封禅等礼仪与西部族群建立和平交往,汉武帝在泾川回山建祠奉祀,将西王母信仰纳入最高祭祀体系,标志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在陇山古道上的深度互鉴。到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代、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代由官方主持重修王母宫等史实,更印证了其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凝聚力。在当代,西王母信仰不仅在台湾省内是政界、商界、文化界及民间共同崇奉的中华文化象征,也是联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寻根溯源的重要文化名片。这种以共同信仰维系的文化和血脉认同,在两岸民间架起跨越万里山水阻隔的情感桥梁。如今,西王母文化更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和合共生”理念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并将随着“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深度实践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古老而鲜活的精神资源。
(三)富贵长寿——始终陶染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西王母文化自古便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神话中西王母掌管的瑶池蟠桃三千年一熟,食之可长生不老,这一意象衍生出“寿桃献瑞”的民俗传统,至今仍是生日庆典与老人贺寿的必备礼品。而她赐予后羿不死药救赎生灵的传说,更将健康长寿升华为超越生死的精神信仰。在民间实践中,泾川西王母庙会的“拴福锁”“拴红”习俗,信众将写有心愿的锁状挂饰系于宫观古树或在手臂系一段红布(绸),祈求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健康幸福。台湾省信众则通过“王母药签”习俗,将中医药理与信仰疗愈结合,形成独特的健康文化。在现代社会,西王母文化的吉祥内涵更被赋予新的活力,据统计,每年在泾川西王母庙会期间,来自包括台湾及全国各地的游客超5万人次,其中70%参与者明确表示是为了祈求健康长寿。地方政府则顺势挖掘“西王母养生文化”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开发出包含玉石药枕、养生膳食等20余种文创产品,带动区域经济的同时传承文化遗产。这种将古老信仰转化为现实福祉的文化创新,既延续着“福寿康宁”的民族集体记忆,也为构建健康中国提供了传统智慧与现代实践交织的生动范本。
(四)团圆亲善——始终承载着人们对和善共融的社会理想。西王母文化自古便是中华文明中“团圆”与“和谐”的象征符号。神话中西王母主持的瑶池宴会,群仙毕至、共品蟠桃的场景,不仅塑造了天界团圆的典范,更衍生出人间中秋祭月、家族团聚时供奉“西王母团圆饼”的民俗传统。在跨地域交流中,这种和谐特质尤为显著。在古代,正如明代《重修王母宫记》所载:“路当孔道,古今名士登览祗谒,题咏甚富”“延宁甘肃诸镇文武重臣,以及奉命总制、经略、抚按,册封出使外夷大儒、元老、名公、硕士,百五十年来经此者,不知其几。”形象地展示了过往文公大儒不论身份贵贱在此团聚、拜谒西王母的盛况;在当代,台湾省3600余家西王母宫庙持续组织信众回泾川祖庙朝圣,近十年累计10万余人次的“跨海团圆”,使得西王母文化成为两岸民间情感联结、团圆交融的重要载体。据台湾学者研究显示,参与西王母文化活动的群体对“社会亲善度”的认知普遍提升15%,其“和而不同”的精神更深度融入城市社区治理。如今,台胞、海外华人寻根到泾川拜谒西王母,这种从神话宴饮到现实共生的文化嬗变,既延续着“天下一家”的古老智慧,也是团圆的文化寓意变成现实的生动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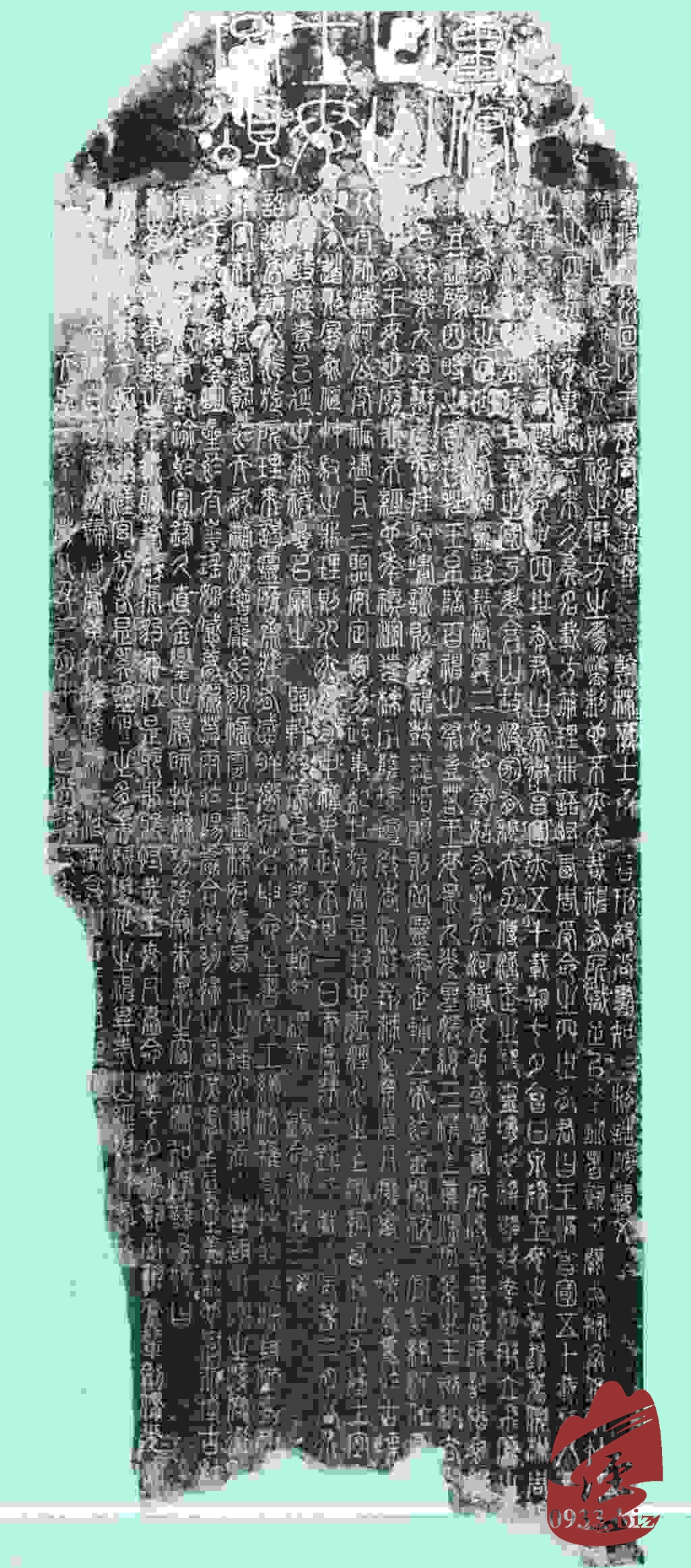
三、国家非遗:西王母信俗的传承赓续
作为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地,泾川以“西王母祖祠”为依托,形成了集祭祀、庙会、民俗活动于一体的信俗体系,并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文化传统既承载着深厚的地域认同,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文化纽带与精神滋养。
(一)祖庭圣地的文化符号,展现了西王母信俗强大的凝聚力。泾川西王母信俗的核心载体是始建于西汉的西王母宫,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被尊为“西王母祖祠”“天下王母第一宫”,是海内外信众公认的西王母朝圣中心。始于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举办的千年古庙会和依托七月十八日西王母诞辰庙会举行的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活动,来自海内外数万民众自发参与祭祀,以“取圣水”“献五谷”“挂福带”等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种以“祖庭”身份为标签的民俗行为,既区别于神话叙事,又不同于道教科仪,形成了以民间自发组织、两岸代际传承为特征的信仰生态。
(二)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展现了西王母信俗坚韧的生命力。泾川西王母信俗的活力体现在民俗活动的多元表达中,王母宫庙会不仅是民俗活动,更是商贸集会、技艺展演的公共空间。水会巡游、秦腔表演、美食物产、剪纸刺绣等民俗项目在节庆中复苏,带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强化了民族文化认同。来自台湾省和东南亚等地的信众组团赴泾川谒祖,通过“共祭王母”“朝拜母娘”等仪式,构建起跨越海峡的文化共同体。近年来,当地将传统信俗与文旅融合,推出“民俗节会”“蟠桃诗会”“王母宴”养生美食、非遗研学、蟠桃采摘等项目,使古老信仰焕发出现代生命力。
(三)民俗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展现了西王母信俗独特的创新性。作为中华民族“母性崇拜”的活态样本,其“崇德向善”的核心理念,为地方民俗文化注入了精神凝聚力。当地民众通过祭祀仪式、家族传承,将西王母文化中尊崇祖先、倡导美德的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既延续了乡土社会的伦理根基,又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文化认同的源泉。信俗中“献祭五谷”“采取圣水”等传统,成为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乡土教材,引导人们注重绿色发展理念与传统生态伦理的深层共鸣。此外,泾川信俗还架起了互动交流的桥梁。通过“西王母文化论坛”“共祭西王母”等平台,地方性的民俗活动被转化为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资源,在同拜母娘、同唱祭文等仪式中,使得中华文化“敬天爱人”的精神内核得以彰显。
西王母形象的变迁,其实是人们审美和心理倾向的一个演化过程,体现的时代特征与各个时期人们的理想追求相吻合。伴随其形象演变形成的文化内涵特质,在中华文化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诸多文化元素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历经千年传承,已从地域性文化符号升华为凝聚中华儿女情感的共同精神坐标。
相关新闻
精彩推荐
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注有“网行风”或“HUGO”的稿件,均为泾川网行风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为“泾川网行风”。
2、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