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之神:完颜氏家族的神“影”和家族神庙
【摘要】甘肃泾川完颜氏的物化之神与祖先崇拜不仅仅是民间信仰,还包含与其宗教表象同样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背景,尤其是文化身份的诉求。本文尝试从完颜氏民间信仰中神明"神力"或者"灵力"入手,认为神明法力的大小是通过作为媒介的"物"来传达的。民间信仰对其合法性的争取是通过借助有形"物"的传统资源和乡土价值,从而不断重构其潜在的文化内涵,以达到信众群体对身份和尊严的双重诉求。
【作者】杨田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期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关键词】民间信仰物化神文化身份
【基金项目】2017年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7M612783);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海外青年人才引进计划博士后资助项目
一、物的宗教人类学转向
学界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角度:认为民间信仰是社会全景的反射[1];民间信仰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而发展[2];民间信仰具有深厚的地方性文化基础[3];存在超越并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的民间信仰[4];民间信仰存在“地理空间”的结构。[5]现有研究多从宏观意义上对民间信仰的脉络进行区域性整体把握。然而,在民间信仰中,普遍存在大量依历史变迁而不断构建并赋予宗教意义的“物”。有形的“物”在民间信仰和信众的精神层面发挥作用,并且因特定场景和环境的转换影响信众的精神状态。
物的文化转向是对物文化认知和价值塑造的重新定义,物由原有的物质形态变为文化的物,体现出多精神层面的意义。人与物的互动,不仅局限于简单的单方让渡,其互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延长和再构成。由此看来,物的文化转向同样可以用于解释民间信仰。在宗教的语境下,有形的物被赋予特殊的文化内涵和隐喻意义,使得原本人造的物因其所赋予的神圣角色而意义非凡。人们致敬并且维护的并非某件有形的物,而是物所承载的宗教意义和角色。因此,从文化化物的角度出发,探索作为媒介的物如何在民间信仰中联通人神,圆融家族,传递家族记忆,表达身份诉求。
民间信仰作为非均质化的信仰(heterogeneousbeliefs);是通过经文、价值观、神话等文化化的物来连接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这说明了所有的宗教都是物化的,是被构建出来的,[6]“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产物,还是一种生产过程”;在这个体现文化的生产过程中,物作为媒介的文化意义被不断升华,[7]①物不仅成为可以沟通仪式、献祭、朝圣、沟通的媒介,也可以帮助解释宗教实践(Prac ̄tice);因而探索宗教文化结构。萨满教通过粘合物态化的“体”和心态化的“悟”从而“入悟返体”的神者意志是通过“可触、可视、可闻、可觉”的形者来沟通贯穿的,这里的有形之物便可等同于完颜氏物化的神,[8]②民间信仰中的神明既是社会权利的生产者又是其所生产的产品,神明拥有掌控信众世俗生活的话语权,同时也拥有塑造信众家庭生活中彰显性别关系和定义身份价值的影响力,[9]基于物在信仰研究的深远影响,使得物的宗教人类学转向成为可能。民间信仰中神灵法力的大小也可以通过作为媒介的“物”来传达。物的神力不仅仅来源于个体或群体性的崇拜仪式,而是来源于其物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涵盖了物的特殊形式的形成,文化机制天生赋予的神力和信徒的社会影响与物的互动。
甘肃泾川完颜氏后裔是一支以祖先神为信仰主体,典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基于长期对甘肃泾川完颜氏历史来源的研究探索,并结合陕西岐山洗马庄王上、王下村以及完颜鄂和墓的调查得出结论:泾川县完颜村九顶梅花山上供奉的金代完颜宗弼之子芮王完颜亨(?-1154)和金末帝完颜承麟(?-1234)之墓为族人虚构构建,泾川县完颜氏与岐山完颜氏为同宗。泾川县的完颜氏主要有两支来源:一支为金末活跃在关陇地区金哀宗完颜守续之胞弟完颜守纯之子完颜鄂和的军事势力;另一支则是明初陕西岐山洗马庄完颜琳(守纯后人)调任平凉副帅为九顶梅花山上朱元璋第九子韩宪王守灵而落籍泾川,其子孙也因完颜琳为官而保留完颜姓氏。
完颜村内保存有完颜氏家族祠堂,门口手书牌匾“追本溯源”。祠堂由正殿、左右厢房、后院和山顶亭组成。祠堂内立有太师都元帅金兀术纪念碑林,碑林共有十一块碑组成,属金朝历任皇帝纪念碑。院内有完颜阿骨打战马戎装雕塑。家族祠堂正殿内设有供奉祖先遗像的家族神“影”的神龛和(黄绳)“皇神”等家族圣物。左右厢房存储祭祖用具,祠堂院内还有顶部雕刻海东青的纪念柱。完颜氏家族信仰主体之祖先神,即金王朝历代皇帝和后人构建的埋葬在九顶梅花山上的芮王完颜亨和完颜承麟。物化主体(MaterialObjects)参与集体身份的认知与巩固,甚至服务于群体间的边界认定,[10]由此说来,物化的宗教也不仅仅是物体本身,或为身份构建物化的仪式而已,仪式发生的地点—家族祠堂本身,也是宗教的物。从完颜家族神信仰之“圣物”入手,透过其历史脉络、文化认知和集体记忆阐述完颜家族神“影”和(黄绳)“皇神”并不仅仅是单独存在的、互不相关的崇拜偶像。完颜“圣物”作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媒介,稳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侍奉子孙之间的关系,将人神紧密结合,并且不断动态地丰富发展完颜家族的信仰生活。通过研究完颜氏家族的仪式,从而发掘作为象征性的家族神是如何被概念化并且具像化的,是以何种形式进入信仰者的生活空间并建立长期关系?因此,深度探讨物化神的构成、媒介和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在对献祭仪式、信仰结构和区域文化网络的考察过程中,尝试从物化神具像过程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物的宗教媒介属性,尤其是讨论物化的神是如何在世俗世界获得神力。认为完颜氏家族物化的祖先神“影”作为物化的神媒是建立家族亲属血缘关系、联系神与人并且增强两者在宗教信仰中交织的纽带。最后,通过完颜氏对物化神构建的意图探索完颜氏信仰的变迁走势。
二、完颜氏家族物化之祖先—“皇神”
完颜氏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举行祭祖仪式“叫冤会”;家族成员在族长的带领下在家族祠堂举行女真萨满祭祀活动。完颜氏族人追溯祖先至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他们珍视祖先的姓氏和世代传承的家族记忆,以金宗室之后自居,认为自己及子孙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①从当代完颜氏祖先神信仰的物化与建构,程序化社会空间的实用主义出发,到仪式实践手段的饱和凸显物化神作为地缘纽带的动态呈现。
(一)构建精神传统:完颜氏家族祭祀祖先神“影”及其物化过程
对传统的构建来源于象征、神话、仪式和有深刻内涵并滋养信仰的文本,以及神话形成中的历史记忆一致性,精神的信念及其直接的构建符号和隐含意义是宗教信仰和人本主义的传统,[11]完颜氏子孙后代基于其所在的现世生活和认知共同构建积累形成了家族神话并逐渐将其精神传统物化,因而聚形而通神。
完颜家族祖先“影”是完颜氏家族世代传承保存的家族世代祖先遗像,被家族成员视为等同于祖先皇帝的圣物。祖先神“影”上,自上而下一共绘有38位人物,分别是10代金代皇帝,1代宗王和27位臣属组成。完颜氏祠堂正殿内现悬挂第4版复制的“影”。据史料记载已知的完颜家族祖先神“影”一共有4个版本:最初的版本始制于金代ꎻ第2个版本复制于明代,由家族成员交替保管,一直沿用至20世纪90年代ꎻ第3个版本是根据明代“影”的照片复制于2002年,并附有下注:“此原画为明季布制,长九尺宽七尺,是完颜家族祭祀世代祖先遗像,已失,拟民国二十五年张东野记,马因摄影,请齐敏轩先生于二零零二年绘画复制,画面增显原画太师完颜宗弼被隐匿之貌。监制:完颜斌、完颜画、完颜麦、完颜银、完颜成辈、完颜东正、完颜明正”②。第4版本完成于2013年,并有注:“宋.金王朝十位帝王及将领金兀术造像我完颜氏族世代曾已供奉三百多年的金王朝先祖,手绘影像乃明末清初画师所绘,幅面长九尺宽七尺,设色古朴,姿态生动,可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遗失,实属我族人之一大憾事,后在县博物馆找到民国二十七年由县长张东野经管拍摄的已发黄且模糊不清的影像照片,为使族人不忘族誉原源,并供子孙后代长期陈列供奉,传承先民八百多年以来与当地兄弟民族和谐共荣之遗风,共建和谐美好未来,我们邀请县文化馆书画家刘文君以影像照片为基本依据,于二零一二年三月重新绘制此金代先祖影像,以弥补族人心中之缺憾,使之香烛延绵,永传后世,愿社会和谐民族团结,未来华夏更美好。完颜斌完颜玺主持并撰文作记壬辰二月刘文君画立书”。“影”两旁附有对联“迢迢七千里幽居安定,悠悠八百年繁衍生息。玉明撰句文君书二零一二年阳春三月吉日”。
至于完颜氏根据照片复制祖先“影”的原因,笔者向一位家族长老询问明代“影”的去向时,得知有完颜氏的“不肖子孙”将明代的祖先神“影”变卖给外人的故事。
“造孽啊,把老先人都能卖掉的人,他打算把‘影’到兰州去”。一声长叹之后,老人抽了一口旱烟,眼神垂下来继续说“这个娃后来心脏病突发死在路上了,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个影一定在呢,在他女儿手里,也一直没有消息,不知道现在到底出手了没有,也不知道到哪里找去呢么...”
老人黯然的神情中包含了对家族失去世代传承祖先神“影”的惋惜,也包含了对变卖祖先遗像的“不肖子孙”的失望。在老人的眼中“影”不是一件简单的物,而是作为祖先神的化身,是证明完颜家族金朝贵族身份的重要证据。明代版的家族神“影”被完颜氏子孙珍藏保管了几个世纪,是作为完颜氏家族祭祀活动中最神圣的物件,象征着“影”中每一位祖先神对后世子孙生活鲜活的参与和庇佑。承载着完颜氏家族对自己曾经的“女真”身份的遥远记忆、对故国和历任先皇祖先的追忆和对后世子孙的教导准则。完颜氏子孙对神“影”的变卖是将承载完颜氏家族深厚精神意义的“神”降格成了“物”;一件用于交换并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文物”或者是流通的商品。
完颜氏对祖先“影”的共同感情纽带来源于村庄中完颜氏子孙共同的姓氏和对祖先的追忆,那么完颜氏对祖先神的亲近和感情应该如何被概念化?首先,完颜氏将感情的亲近寄托于有形的“物”ꎻ其次,完颜氏对祖先的感情亲近也不仅仅是将“影”奉其为神明而崇拜,更重要是其物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重绘“影”的材料选择,嵌入的历史文化机制以及从供奉传达的文化内涵。物化的祖先用“影”的方式传达,并成为完颜家族因血缘而建立的神与人之间流动于当地民间信仰生活的介质。完颜家族2002年版祖先“影”是根据明代祖先“影”的照片复制而来的。从画面上看,完颜宗弼家族的地位极其突出,完颜亨也位列其中。宗弼一支被画者突出于整体画面,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世代保存祖“影”的泾川完颜氏追溯他为自己的直系祖先。2002版祖先“影”下注中强调了“画面增显原画太师完颜宗弼被隐匿之貌”;说明画师基于明代版本“影”;再次突出了完颜宗弼的形象。有学者认为明代“影”的绘者之所以隐匿完颜宗弼的形象是因为明代岳飞的故事被广泛流传,完颜宗弼等金国人物被丑化,画者不敢公开宣传完颜宗弼,[12]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原因有三。第一,完颜氏祖先“影”仅用于家族祭祀,而且家规中明确规定“凡非完颜氏者不得进入家族祠堂”;加之完颜氏祭祖仪式的隐秘性,那么能接触到完颜氏“影”的人势必仅是拥有完颜姓氏的族人。完颜氏对自己直系祖先的情感不太可能受汉人崇拜岳飞的情怀而动摇,更不可能因此而隐匿祖先的样貌。第二,家规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凡完颜氏子孙不听不看«说岳全传»;不唱«草坡面礼»«八大锤»«反徐州»等有关岳家将的戏曲,不允许与岳姓通婚。因为完颜氏认为这些文本包含侮辱自己祖先的内容,这就进一步夯实了推断,完颜氏不会因为对岳飞的顾虑而不敢公开祖先的样貌。第三,从2002版完颜氏复制的祖先“影”和访谈内容看,完颜氏对画师作画的影响力和最终版本的确定都倾注了完颜氏精英阶层基于现世对祖先的构建因素。且不论明代“影”迫于何种压力使得完颜氏子孙隐匿完颜宗弼的样貌,2002版的“影”确实将其是“増显”了,这种“増显”是后代子孙对先人的英雄主义构建性创作。因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民间信仰有着深远影响,此外结合强大的地缘影响力,民间信仰在权威统治动荡时期蓬勃发展,祖先信仰也会在这个政权宽松的历史性时期进行自我构建和狂欢。
(二)完颜氏家族的祭祖仪式:与“皇神”对话
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是最重要的国家礼制,“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13]。祭祀仪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儒家政治哲学。女真族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古老的少数民族,在公元1115年建立了金王朝。此外,金王朝于1124年打败了辽国,并长期于南宋和西夏之间处于军事优势。金王朝统治期间,女真统治者继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并且接纳了其礼仪,尤其是国家祭祀礼仪文化。重新进行了女真文化对汉文化的整合,奠定了金王朝国家祭祀仪式礼制的发展和确立。金王朝建立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政权,女真统治者都深受儒家思想和汉文化的深刻影响,随着政权不断集权化,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先进的汉文化更有利于其统治,女真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深度汉化的过程。因此,金王朝政权权威更迫切的模仿汉廷的统治传统和组织形式,确立以儒家为核心的权威正统。逐渐汉化的统治方式瓦解了女真原有的社会结构,同时倾向于汉文化的新的意识形态被逐渐确立起来。泾川完颜氏追忆其伟大的祖先与昔日的辉煌之唯一途径是重现隐匿汉化的祭祀仪式。
神庙(家族祠堂)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如何作为祖先神的传达载体在神与人之间建立精神联系?完颜氏的祖先神当然不能向后代子孙们自我传达意志,而是以作为物化、有形的神“影”、“皇神”(黄绳)、家族神庙以及神职人员等神媒来传达。神明的“灵力”是如何通过人与特定地点的联系不断増显的?物化的祖先神“影”“皇神”(黄绳)以及用于仪式之中饱含隐含之意的“物”来传达神的意志,慰藉信徒子孙心灵。两者的相互协同表现在仪式之中。从物化介质的角度研究神灵的物化形式,表达神庙是祖先神的传达载体,能最大限度地彰显祖先神的“灵力”“皇神”(黄绳)则代表祖先神本尊,续黄绳仪式从隐含意义上传达了亲近祖先和完颜子孙绵延不断的双重含义。
完颜家族祭祖仪名曰“叫冤会”;于每年的阴历三月十五在完颜家族祠堂举行。仪式由十鸣炮开始,家族祠堂外摆放着五门大炮,每门炮有两人负责,一人装弹药,另一人负责点燃火炮。十声响炮代表着对金代逝去的十位皇帝的崇敬。炮口要对准东北方向鸣响,代表对东北故乡的眷念。礼炮毕,击鼓鸣钟共120响,代表金王朝的统治年代。随后,祖先神“影”由责保管专人焚香祝祷后,从包裹的红布中“请”出,悬挂于祠堂正殿的专门设置的神龛处。请“影”之同时,鞭炮礼乐不绝,由家族族长宣读祖先祭文。家族的妇女们进行献碟迎供,妇女们用献碟端来各种面粉和植物油制成的花馍,花馍的制作和样式代表了各个家庭主妇的烹饪水平,主妇们竞相展示自己的手艺以示对祖先的尊敬。她们跟随鼓乐的节奏,将献碟摆放供奉在祠堂的香案上。正殿内,除满摆的祭品献碟,殿内两侧还摆满用彩纸做成的神马和仙鹤,悬挂各色彩纸做成的写有“皇恩大赦天下太平”的纸幡。完颜氏老幼见“影”皆如见祖先,每人需手持焚香,跟随族长与家族长辈三跪九叩,并且跟随族长齐声祝祷:“太祖,太宗,承麟,芮王在天之灵千古,”除了完颜村本村的完颜氏,泾川县城的完颜氏以及从外地奔赴祭祖仪式的完颜氏后人也依次根据家族辈分和社会地位跟随族长祭拜瞻仰祖先“影”。有的家族老者也会满含泪水,仰天长啸,哀嚎对祖先的怀念,并念念有词地对后人讲述家族故事和神“影”上每位祖先的故事。被礼炮钟鼓、香烛黄表和家族精英的虔诚渲染出的祖先神“影”在仪式中显得格外庄重神圣,使得本来懵懂的孩童在家族长者浪潮般的层层叩拜和祝祷词中似乎继承深谙了自己作为完颜氏后人的“贵族血统”,家族祠堂成为家族长者祭祀祖先并且传承教育子孙的场所,也是传达祖先意志和血缘情感凝结的载体,完颜氏家族祠堂门口除了贴有完颜氏家族内部成员送来的花环花圈等纪念性礼物,还有落款为泾川县政府和县委送来的彩纸花圈。献祭仪式是家族的血缘纽带,有深厚的地方化特色。信仰的具像化是通过物来表达的。神庙中的神“影”作为物的具像体,从信仰者和子孙后代那里汲取信仰的力量,与当地社会的教化情境相融合,传达出神力并得到官方的认可。
祭拜祖先神“影”之后,在族长的指引下,由十几位完颜氏强壮的小伙子将一根黄色麻绳抬出来,黄色麻绳粗壮且长,小伙子们将绳子从祠堂正殿抬出来,置于祭祀的香案上焚香供奉。完颜氏长幼再次齐齐跪拜敬奉。黄色麻绳有着深厚的寓意,是“皇神”的谐音,代表着完颜氏祖先神本尊。完颜氏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着对祖先隐匿的祭祀,而不为外人所知。长久以来,完颜氏的身份是被族人刻意隐藏而避免元朝统治者的追杀的,①因此,完颜氏以谐音“皇神”寄托对故去“皇神”的隐痛思念与追忆,续黄绳的仪式由参加祭祖的完颜氏子孙们参加,每人皆手持一股绳由专人续接在黄绳的一头,最终与原有的绳子拧结成一体。子孙越多,绳子就会越粗越长,显现出完颜氏的人丁兴旺和对祖先的敬意,从续绳的新旧也能看出来之前祭祀的痕迹,从而推断参加的人数,或许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祭祀场景,这条黄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完颜家族表现祭祀情景和人口的记录,更是一部完颜家族祖先神在场的家族人口谱牒。黄绳续完后,小伙子们将黄绳的一头抬到家族神庙顶的小山并绑在一棵老树上,另一头在家族神庙中固定。由萨满法师跳神之后,寓意祖先降临。众人将祠堂正殿中的彩纸仙鹤、神马神鹰等请到山上,固定在木质的滑轮上,依次沿着黄绳滑送至山下祠堂中。仙鹤神鹰如从天而降一般,落入祠堂之中,老族长带领子孙高呼“皇恩浩荡,赐福救民,普降吉祥,皇恩大赦”;寓意仙鹤神马等神兽是“皇神”赐福子孙。神兽们降临到祖先祠堂之后,子孙族人将他们抬至泾河边焚化,寓意将祖先赐予的神兽送回天宫并感激祖先降临的祥瑞。
(三)完颜氏家族的神物、神庙和神媒:物化祖先的载体
祭祀典礼与祭祖仪式是完颜氏沟通神与人的手段,将无形的祖先神物化为有形具像的“物”并通过作为载体的“媒”来传达。如果说家族祖先神“影”犹如子孙们面见的祖先,那么续“皇神”(黄绳)仪式则是完颜氏后人对家族香火绵延的交代和保证,在黄绳上放飞仙鹤与神马是祖先神赐福子孙的寓意,以此方式,祖先神灵被物化,通过仪式的表现和萨满法师与神的沟通,物化的祖先神在家族神庙中“显灵”。从这个角度来说,物化的祖先神使得子孙们能够感知到祖先的在场与通灵,更能感受到祖先神的赐福,从而加深对家族血缘的认知,起到凝聚子孙的作用。物化的祖先神,因其具化形式得以更加深植于子孙后代的社会生活中,并以血缘关系自然地结为更加亲密的关系模式。
祖先神的物化,包括祖先神“影”的复制、黄绳的延续等与彰显祖先神力载体的家族神庙都活跃于完颜氏日常生活中并通过不同形式的媒介传达出祖先的庇护。神“影”和黄绳承载祖先神的“灵力”;通过家族神庙的载体,仪式和萨满法师演绎之媒介而显灵。这样,具像化之神物、神庙和神媒成了完颜氏家族信仰系统中相互协调,互为层次的基础。首先,物化之神赋予完颜氏祖先神以“人格化”;联通子孙之精神信仰与祖先之神力。子孙们可以从有形的物感知到祖神的存在。物化之神从此意义上拓展了祖先神“神力”的边界。神之具象化存在也使得信众在心态上产生与神的亲近感。完颜氏神“影”和“皇神”(黄绳)因其与完颜家族传承的集体记忆相关,其世代建构的物化之神不仅是家族传承记忆的媒介,也是教导子孙、延续、发展其信仰系统的方式,其次,家族神庙因家族与姓氏的私有属性和极强的地方性,增强祖先神的神力,联通信众与特定地点之间的关系。家族神的神力因神庙的存在而增其神力,固其地位。建立在村落中的家族神庙是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共同的祭祀场所。完颜氏恪守的族规之“凡完颜氏者,不得进入祠堂”就是对祠堂的神圣性、隐匿性和排他性最好的诠释。家族传承的规矩也因其本身带有祖先遗命性质而充满神圣性和无可挑战性。是完颜氏子孙精神中对祖先的逝去荣耀和自己“女真人”身份的追忆。人们将家族神庙作为载体,用多种形式追忆女真的全盛时期,回顾他们强大而光荣的历史。比如盛大的祖先祭祀仪式,家族精英关于祖先的出版物和因女真传说而构建的家庙建筑及住宅。完颜氏将集体记忆与家族传说中的祖先物化为有形的存在。并且在祖先神庙这样的特殊的地点,基于主观对过去构件的偏好和有组织的祭祀仪式呈现出来。第三,神媒以人或物的形式存在,深刻地理解神媒在联通物化祖先神和信众精神的文化意义,从信仰系统的角度重审祖先神信仰的社会影响力。神媒以神庙为中心,通过人的神媒和物的神媒方式而传达神灵的意志。物化神媒以多种形式代表祖先神之灵存在依附于有形的物。神物具化神力,承载祖先神之神力。另一个方面,由人充当的神媒如萨满法师相比较物之神媒则更加灵活。他们能更直观的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信众,并用语言、仪式和感情来呈现神力。两种神媒的形式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三、结论与讨论:民间信仰反思
信仰定义信众的价值观并塑造其文化身份,[14]神灵是社会权力的产物。完颜氏物化祖先神的过程凸显其对世俗权力和对自己女真身份认同的诉求与抗争。从历史上完颜氏女真人自金代晚期近似完全汉化的程度来看,完颜氏的信仰系统体现国家秩序。“当金王朝全面崩溃之际,完全的汉化使得女真人得以生存”;这也解释了泾川完颜氏之所以能够逃脱元兵的追杀,保存族人和传承祖先姓氏最重要的原因,即“汉化的内在力量,似最终来自以男性为主宰的汉化宗教,其核心是祖先崇拜”[15]。女真族人长期奉行中国儒教正统文化,尊崇以汉为正统的心灵历程,与汉族人长期交互融合,其祭祖仪式的构建和信仰结构的整合势必体现出民间信仰的最终解释权在于主宰的国家统治话语。
国家意志根据政权结构反作用影响构建民间信仰的神明。但是,完颜氏的信仰系统也因其从贵族到土著的过程而呈现动态的流动。第一,其信仰存在游离于正统权力结构之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不是政权系统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等级的简单反射,而是因信仰长期构建过程中不断地土著化,从而结合并糅进诸多能反映当地潜在社会现实的元素和认知。例如完颜氏祭祖仪式中的萨满跳神仪式,法师的穿着明显杂糅进了道教的元素和地方传统,法师动作和服饰彰显了神明崇拜的动态转变。第二,其信仰系统不断被边缘化,祖先神的神力逐渐呈递减趋势,从泾川县区域群神多元信仰的社会环境来看,当地地方信仰系统中一直存在一个以西王母信仰为主的多元信仰系统,再加上结合因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田野数据来看,完颜氏从唯一的祖先神信仰开始出现向西王母信仰和其他多神明信仰转向的端倪,第三,完颜氏家族精英对信仰的“满族化”构建和民族身份的试探,从象征与隐喻的物化祖先到构建宏大的满化仪式与信仰,完颜氏精英力图通过展示与众不同,得到官方的承认而试探改变民族成分的可能,而当地政府则是更加看重完颜氏展示的“民族特色” 所带来的潜在经济意义,自2013年起,政府从开发全县旅游资源和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出发,对完颜村进行整体规划,投资建成了完颜部落古寨、完颜洼文化广场和带有金代风格建筑元素的民居等,2017年,“泾川县王村镇完颜村美丽乡村计划”基本落成,完颜村因政府的参与引导而被建造成以游玩、观赏、餐饮娱乐、民俗体验、访古溯源为主的拥有完整配套设施的民俗风情旅游区,完颜氏的历史遗存和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是完颜氏物化神明信仰合法性的基础,地方政府对完颜村旅游资源的整合和重塑保证了其文化权威,旅游作为国家行为的前沿,在文化创造和国家身份塑造中保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18] 结合宗教与旅游来看,国家在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只允许那些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呼应,协调和谐社会的建设,并且不挑战国家统治权威的民间信仰和地方神明存在,地方政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在完颜氏家族精英构建和创造的文化记忆基础上,以旅游经济为目的而规划建设的完颜文化风情园及其配套附属建筑,官方构建并认可完颜氏的女真身份及其尊严,这种官方引导的记忆重建过程将完颜氏物化祖先的信仰载体视为潜在开发的地方文化特色而大力发掘其市场价值, 物化的宗教符号最终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 Wolf,A. Gods,Ghosts,and Ancestors.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M].W.Arthur. Stanford,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74:131-182.
[2] Watson, J.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 alone the South China Coast,960-1960.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M].A.N.a.E.R.David Johns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292-324.
[3] 范丽珠,欧大年. 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47-164.
[4] Wang,M.Place,Administration,and Territorial Cults in Late Im 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From South Fujian[J].Late Imperial China,1995,16(01).
[5] Lagerwey,J.China:A Religious State[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7-22.
[6] Asad, T.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 er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
[7] sity Press,1993.
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M]. 王超,朱健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5-26.
[8] 纳日碧力戈.“体物”之人类学观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2(02).
[9] Weller, R.a. M. S.Unruly Gods: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17.
[10] King,E. F.Material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M].London:Routledge,2009:5-9.
[11] Maes,C.Formation Tradition,Its Transmission,and Spiritual For matio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on and Morernization[M].M. Y.Wang,Xuanmeng George F, mcLean. Washington,D.C,The[12]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 Philosophy,1997:406.
何志虎,贺晓燕.泾川完颜家族祖先遗像考释[J].甘肃社会科学,2005(02).
[13] 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0:525-1771.
[14] Weller,R. a. M. S. Unruly Gods: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79.
[15] Ho,P.-T.In Defense of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8(57).
[18] Sutton,T.O.a.D.S.Introduction.Faiths on Display: Religion,tourism,and Chinese state[M].T.O.a.D.S.Sutton, Rowman& Littlefield P ublishers,Inc. Introduction,2010:13.
相关新闻
精彩推荐
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注有“网行风”或“HUGO”的稿件,均为泾川网行风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为“泾川网行风”。
2、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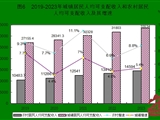


 [
[
 [
[